前言
从弗洛伊德提出“人格结构”的那一天开始,就被众多的批评家应用到了对人的批评之中。
1936年,曹禺的话剧《日出》在一定程度上有弗洛伊德思想的影子,但在主人公陈白露的性格中,却有弗洛伊德关于“三重人格”的思想。
陈白露的悲剧,可以说,是由两种不同的“自己”与“自己”之间的相互碰撞而产生的,而这种从心灵深处产生的矛盾与冲突,则构成了《日出》一剧的基础框架。

此外,曹禺也十分关心在“钱欲”的影响下,陈白露的性格变化、精神冲突、精神冲突等问题,也反映了她在“钱欲”的影响下所经历的种种变化。
所以,要剖析陈白露那错综复杂的个性特征,就只有把他置于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去审视,方能给出陈白露的创作动机与悲剧性的命运以一个合理化的诠释。
一、陈白露的三重人格映射
1.“自我”、“本我”、“超我”
弗洛伊德在他的著作《自我与本我》中说:
“把人的心灵分为有意识和潜意识,是对人的心灵的一种必要的先决条件。”正是基于此,弗洛伊德才创造了三种心理术语:“自我”、“本我”、“超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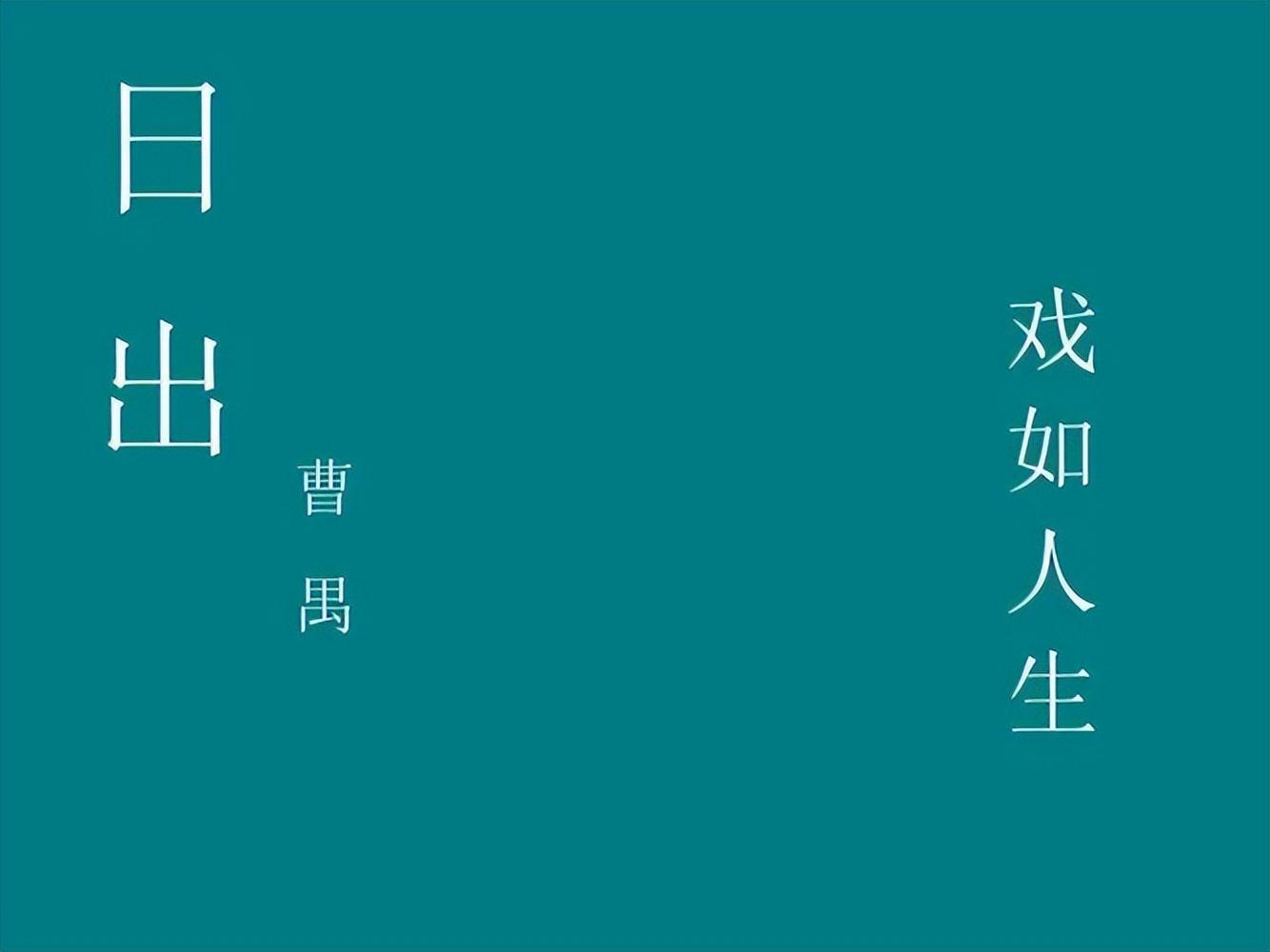
简而言之,“本我”就是“管辖”在人类潜意识里的那一块,也是人类性格中最基本的一块,与人类最基本的渴望相一致,而“快乐法则”,就是控制“本我”的法则。
陈白露隐藏在心里的,就是她自己。有些人把陈白露看成是“陈白露”以前的“竹均”,意思是在她未受城市情欲的侵扰以前,她的本性是纯洁的,善良的。
本文作者以为,弗洛伊德着重于人类的本性,即人类的无意识空间中的事物都具有需要性,是人类从诞生开始就具有的个性。陈白露的“竹均”形象固然美丽纯洁,但这是她所处的社会生活所造就的一种个性。之后,这个“人格”成为她心目中的“完美”,让她在浮华和浮华之间的人生更加痛苦,从而产生了她和真实“自我”之间的心理冲突。

所以,竹君这个「陈白露」,实际上就是超我的投影。“竹云”虽然已经成为了历史,可是在陈白露的心里,却依然有一种美丽的感觉,只不过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份感觉越来越淡了。若非方达生这位大才子的出场,恐怕陈白露也就慢慢忘记了过去的自己。
陈白露出生在一个书香世家,自幼和方达生就是一对发小,又是爱华女子学校里的尖子学生,学识渊博。可就在这时,她的爸爸去世了,这突如其来的变化,让她的生活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

她曾经说过:
“我是一个人打拼的,既然我已经离家出走了,没有亲人和朋友的帮助,我能做的,就做,如果做不到,我就死。”
然后,她就去了大都市,做了电影明星,做了舞女,成为了一名非常受欢迎的社交明星。
纵观她的拼搏历程,可以看出她的聪慧,美丽,大方,自负,骄纵,爱美,任性。她有一种对白雪情有独钟的洁癖,正显示出她那个时代的高洁品格。但是,对于她在新时期妇女解放思想中所表现出来的个性特点,我们却无法做出准确的评判。

2.有形与无形之间的界线
具体而言,弗洛伊德认为,有形与无形之间的界线,也许还没有这么清楚:
“到目前为止,我们所拥有的仅有的指引,就是区别有形与无形之间的区别;最后,我们将会发现,这种区别性符号的含义是何等的模棱两可。”
陈白露的性格就是这种特征的写照。陈白露的原始之美,是由其与生俱来的“原我”与后天培养而成的“起我”两种因素综合而成的。

但作者以为,陈白露之“本我”仍是以享受为第一位,并带有都市中人的浮华与虚荣心占主导地位的个性成份。曹禺没有表现出陈白露一步一步往下掉时那种错综复杂的情绪。
我们可以理解一个十几岁的女孩,为了生存而离家出走,承受了多大的压力,但是,陈白露的下意识里,肯定也是和城市里的人有共同之处,所以她才会拒绝方达生的帮助,才会沉迷于城市里的生活。这种“自我"和"超越自我"的结合,就造成了陈白露这个人物的悲惨形象。
“我”是一种处于“我"与"超越我"中间,受到了客观世界的制约,它驱使人们在客观世界中学会了怎样去实现自己的需要。陈白露的“我”,是一个在繁华大都市里挣扎求存,在现实和心灵的矛盾中努力保持着一种均衡的人。

弗洛伊德在对"自我"的诠释中提及:“自我主要是通过对自身定位的影响而产生的”。
简而言之,这是为了让他能够更好的把握“自我”和“自我”的关系。然而,陈白露的悲剧性却恰恰是因为她无法找到二者之间的均衡,“超我”的呼唤与“本我”之间的冲突,从而造成了陈白露的自尽。
二、角色间的替代性满足
1.自我的替代一花翠喜的妾妇之道
恩格斯把一种类型的人划为没有“自觉的意愿”,而是“甘受奴役”的中空角色。花翠喜很明显就是恩格斯所描述的那种人,作为一个娼妓,花翠喜由于没有自己的主见,只能将她那一片空白而又迟钝的心灵投入到信仰中的“神学”这个神圣的祭台上,一边做着与传统思想完全不同的勾当。

花翠喜从根本上来说,她和陈白露都是“自我”的一部分。但区别在于,她已经彻底抛弃了“人的尊严”,以一种“人是卑鄙小人”的身份,超脱于道德规范,“既然来到了这里,就不要想着要面子了。”引导着她的,就是封建时代男人为妻,女人为妾。
她还用这些话来安抚她:“你还小,你还是有希望的。再过些年,找个正派的,改邪归正,生个儿子,过上幸福的生活。"
弗洛伊德是这样理解“罪恶感”的:
“内疚是基于小我与小我模式的张力,小我利用自己的批评力量来表达自己的指责。”
因此,在“内疚”的影响下,她偶尔也会显露出一种叛逆的个性,那就是“急躁"和“不烦受"。

但这两种叛逆的个性,都是建立在对一个好人家的女人的幻想之上的:半夜想一想,谁不是靠着爹娘吃饭呢?谁小时候不是被人宠着,被人宠着?谁到了年纪,还不是要生孩子,做个老人?呵,大家都是人,哪有那么容易被人欺负的?
正因为如此,她才不可能完全摆脱对男性权力的束缚,而“罪恶感”所带来的自律,总是和她的顺从联系在一起的。而这个反差极大的“自己”,也正是陈白露在不同的生活和生活情境中的一种可能形态。

2.本我的替代一小东西的贞节牌坊
花翠喜的身世跟陈白露很像,很早就失去了母亲,失去了父母,孤苦伶仃,孤苦伶仃,落入了金八的混混头子黑三手里。金八喜欢她,金八对她动手动脚,她说自己很害怕,就给了她一记耳光。
为了处罚她,黑三他们把她饿了一整天,又把她揍得鼻青脸肿,绝望中的她好不容易才挣脱了陈白露的魔掌,跪在地上求饶。对于这个有过如此遭遇的小家伙,陈白露不仅忘却了自己的醉意,更是不顾自己岌岌可危的生命,主动帮了她一把,还收了她为义女。

或许,她在眼前的少女身上,也看到了当年的自己。最起码,他的勇气,他的骄傲,他的自尊,都和他十六岁时一模一样。花翠喜被金八他们欺负时,她的反击完全是一种本能,这种反击正是陈白露内心深处最真实的一部分,这也是为什么她会在金八被小东西揍了一顿时,说了一句:"好样的。"
这一刻,陈白露欣赏的是内心深处隐藏着的骄傲,骄傲,桀骜不驯的“本我”。
假如贫困与饥饿能让一个人变坏,为何不能让一个人在金钱的引诱下隐藏起来的渴望成为一个人变坏的催化剂?这丫头骨子里,也有陈白露当年的几分爱美之心。如果说黑三的殴打激发了她心中的叛逆,那么这十二个小时的经历,很有可能就是让她迷失了自我。

曹禺并没有给予角色心灵上的抉择,他只是在外在的压迫下,将那个小小的事物推向了灭亡的边缘。于是,陈白露那种自相矛盾的“自我”,在这个小丫头身上,并不存在,但她,就是陈白露真正的自己。从这种意义上讲,陈白露努力挽救一些小事,其实也是一种自救。
三、集体环境作用下的人格矛盾
任何一种典型的、经过了较高程度的艺术总结的角色,其内涵都是十分复杂而又富有内涵的,因而也就不可避免地引发了对其的讨论与争议。
《日出》一出,围绕着陈白露的人物形象之争就没有中断。用弗洛伊德的“性格构造”来分析她,或许会让我们更加了解她的命运。

一句话,《太阳升起》展现了一场人类的悲剧性的场景,曹禺在戏剧的表演方式上把主人公的心理冲突给扩大了。也就是因为这些被无限地扩大了的“自相矛盾”的个性,才使得“于白露”一词具有更高的艺术感染力,值得我们去探究。
弗洛伊德曾在《集体心理学和自我的分析》一书中说:
“一个人一旦加入了一个群体,就失去了他原有的个性特征。他将会多愁善感,缺乏责任感,丧失良知,智力低下。他所有的潜意识都被激发出来了,他会做出他过去从来没有做过的事,也从来没有做过的事。”

陈白露所处的大背景,即曹禺所要描绘的年代,是一个历经“五四”洗礼,既追求个性解放,却又为金钱所支配,物欲横流的大社会。虽然她从小就很喜欢城市的生活,但在这个“集体”面前,她之所以会沦落到这种地步,完全是一种“不甘心”的心理作祟,也正是这种心理,让她开始了一种以“社交女神”的名义,以一种“游戏”的方式生存下去。
她曾经对自己的婚事抱有很大的希望,但现在,这一切都成了泡沫,只留下了一片凄凉。
在这段时间里,社会上的腐朽似乎成了她的另一个动力,在见识到了都市居民的可恶之后,她只能靠着“虚荣”来保持内心的平静:“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欺骗任何人,也从来没有想过要去抢劫任何人,我的生命都是由其他人自愿的,因为我已经做出了自己的牺牲。

“我为一个女人做了最微不足道的事,我享受了一个女人应有的权力!”陈白露所有的异乎寻常的行为,都是“对这些无意识的本能的一种宣泄”。
结语
实际上,陈白露所表现出来的,是在城市的物质生活压力下,都市妇女对传统价值观的偏离,也可以说,是在这个功利主义的世界里,人们潜藏在内心深处的一种人类的渴望被唤醒了。

难怪有些学者说曹禺的一切创作都是从他所谓的“原始情感”和“野蛮残留”中产生的爱情情结。作者认为,从弗洛伊德主义的观点来看,这也是对戏剧《日出》最好的诠释。

